周國平曾說:
「人得的病只有兩種,一種是不必治的,一種是治不好的。
人們爭論的問題也只有兩種,一種是用不著爭的,一種是爭不清楚的。」
世事變幻無常,君子不爭炎涼,人生的幸福法則,就是有所爭,亦有所不爭。
不爭,自有世界,也自成境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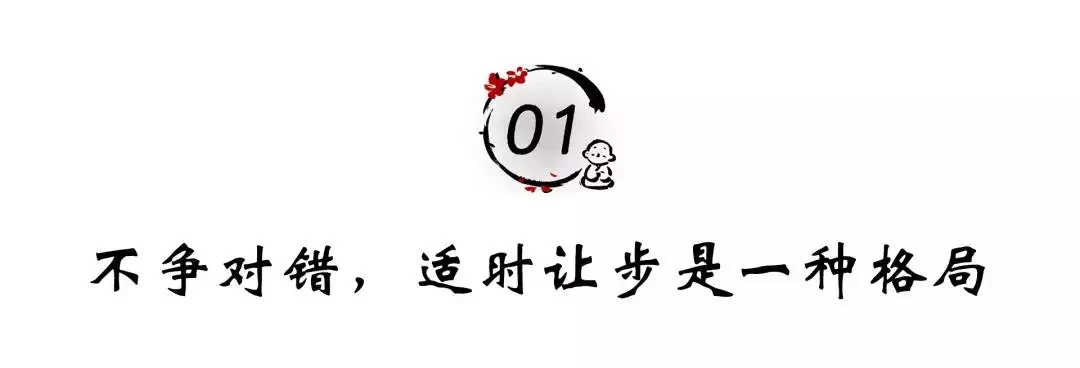
不是所有的魚都會生活在同一片海里,正如不是所有的人都活在同一個層次。
人活一世,難免會被誤解、受質疑,有懂你的人與你惺惺相惜,就有不懂你的人讓你避之不及。
而真正有大格局的人,都懂得知理不爭:
不爭眼前的榮辱,也不在意一時的是非。
正如尼采所說:
「與惡龍纏鬥過久,自身亦成為惡龍。凝視深淵過久,深淵將回以凝視。」
生命寶貴,不該浪費在無謂的爭執上,為無中生有的爛事計較,和無事生非的小人糾纏,最後都是和自己過不去。
聽過一個笑話:
有年輕人看不慣別人的做法,三天兩頭和人吵架,他總覺得誰都跟他作對,生活了無生趣。
鬱悶的他去問智者:
「快樂的秘訣是什麼?」
智者告訴他:
「快樂,就是不和愚者爭對錯。」
他又開始不服:
「不可能吧?哪有這麼簡單,我可不覺得。」
大師微微一笑說:
「你是對的」
就再也不理他。
想要真正的快樂,不如把嘴閉嚴,別爭也不理。
把時間留給自己,把其他留給時間,不在乎就是對一切最好的回擊。
俗話說:
「常與同好爭高低,不與傻瓜論短長。」
退讓不是軟弱,而是一種豁達。
不跟糊塗人講道理,對爛人爛事能做到忍讓而不爭辯之人,才是有大格局的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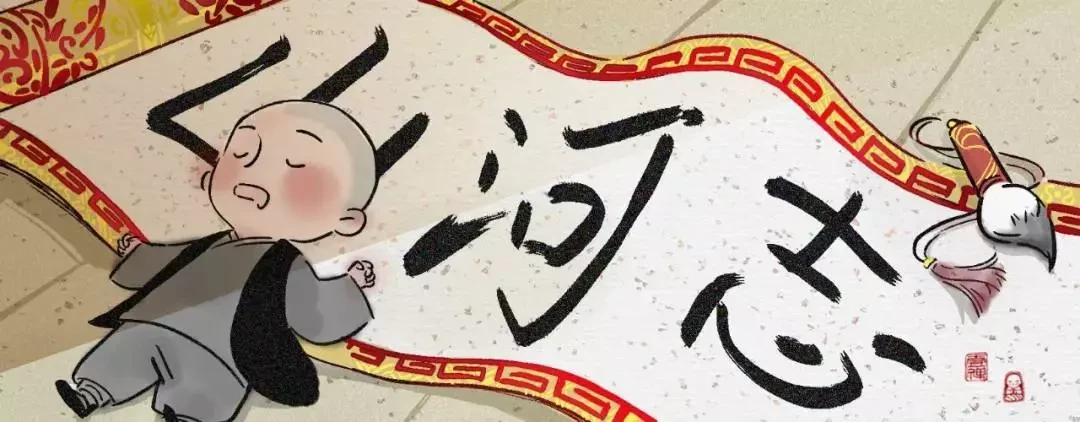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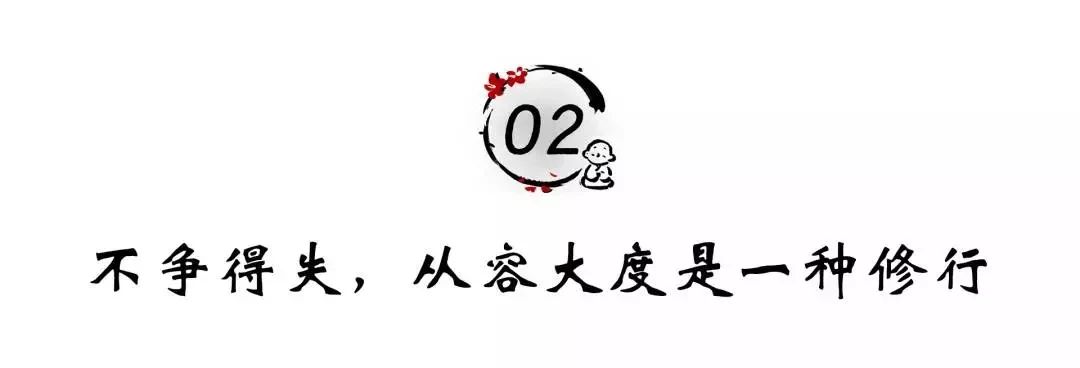
常聽到有人抱怨命運的不公,或抱怨生活的無奈。
誠然,人的一生,總在得失之間徘徊,在悲喜之中輾轉。
正如沈復在《浮生六記》中寫到:
「人生碌碌,競短論長,卻不道榮枯有數,得失難量。」
當人被外界事物所奴役時,一點小事就會把人牢牢束縛。
人生本過客,得失皆隨緣。
等你能做到不以物喜,不以已悲的時候,就能隨時拿得起,亦隨時放得下。
《莊子·田子方》中有這樣一個小故事,肩吾問孫叔敖:
「你三次出任令尹卻不顯露出榮耀,後來,三次被罷官也沒有表現出憂愁的神色,
總是這麼歡暢自適,你心裡到底是怎麼想的?」
孫叔敖回答:
「我覺得官職爵祿的到來不必去推卻,它們的離去也不可以去阻止,這些得與失都不是出於我的自身,也就沒有憂愁的神色。」
一個人對於得失爭得越多,束縛他的東西反而會越多。
相反他求得越少,困擾他的東西卻越少。
人生,本就是一邊失去,一邊得到的過程,
一時的失去,在浩瀚的生命長河裡,渺小如塵埃。
得之我幸,失之我命,與其糾結於過去的得失,倒不如放平心態,過好生活。
往後餘生,把心放寬一點,得失少爭一點,也許一切都會豁然開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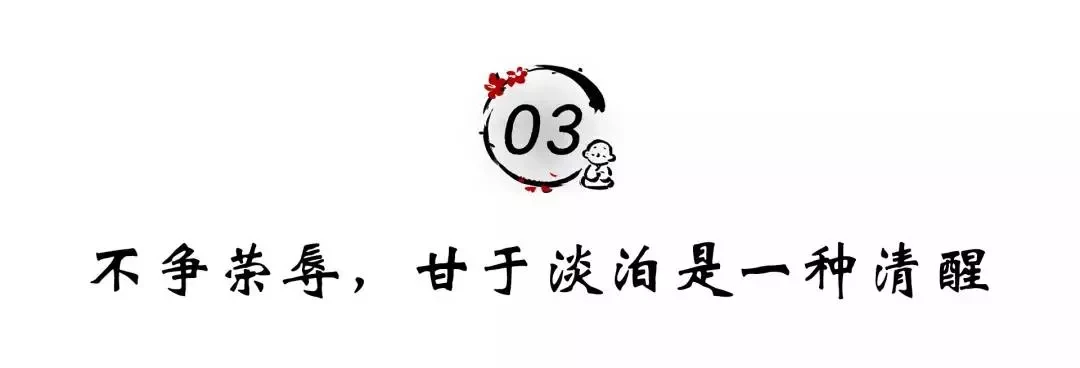
漢代張衡《歸田賦》中說:
「苟縱心於物外,安知榮辱之所如。」
意思是,只要我置身世外,做到心中無物,哪裡還管他什麼光榮與恥辱呢?
常言道,水深不語,人穩不言。
做人除了爭,還有很多高雅的選擇和活法。
山不解釋自己的高度,並不影響它的聳立;
海不解釋自己的深度,並不影響它容納百川。
人生的高度不在於你看清了多少事,而是你看輕了多少事。
楊絳曾翻譯過英國詩人蘭德的詩:
「我和誰都不爭,和誰爭我都不屑,我愛大自然,其次就是藝術。
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;火萎了,我也準備走了。」
這首詩也可以看做是她一生的寫照:
在這熙熙攘攘的世間,多數人都想著出人頭地,追名逐利。
可楊絳不這樣,她讀書寫作,翻譯治學,只是因為興之所至。
面對一生的黑暗曲折,她始終堅定內心,只管做好自己的事;
她的身上始終有一種溫和淡雅的氣質,與世無爭。
在這個世上,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夠去解釋,也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去解釋。
你沒辦法去決定,別人怎麼想,怎麼說,但你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,為人坦蕩,處事清白。
所以,遇事不必急於解釋,凡事不用計較功過,問心無愧即是最好的結果。
周國平說過:
「我從不在乎別人如何評價我,因為我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事,如果一個人對自己是沒有把握的,就很容易在乎別人的看法了。」